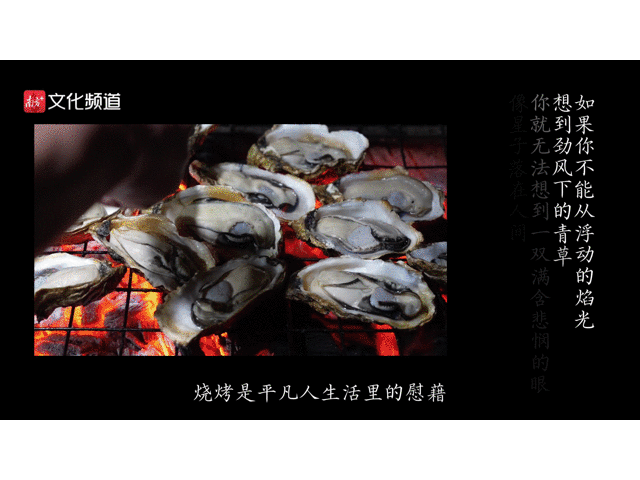(戳视频,对话素人作家温雄珍↑,时长共6分09秒)
烧烤诗人,在炭火上写“人世间”|新大众文艺访谈录②
在鼓风机的作用下,烤炉里的炭火迸发出一簇簇火星,灼热感扑面而来。
温雄珍看到入迷,她把眼前这一幕写进了诗里:“如果你不能从浮动的焰光/想到劲风下的青草/你就无法想到一双满含悲悯的眼/像星子落在人间。”(《黑炭》)
白天,她是童装店的老板;夜晚,她是烧烤店的服务员。此外,她还有一个身份——诗人。温雄珍只有小学五年级学历,却写了2000多首诗歌。去年10月,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在炭火上安居》。
如果说,烧烤是平凡人生里的慰藉,那么写诗就是温雄珍对抗生活的方式,或许,也是她与生活和解的方式。
温雄珍今年51岁了。凌晨1点多,她一边干活,一边感叹:“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天天都得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忙到焦头烂额,就像烟熏火燎的烧烤一样。”
告别
母亲走了,果子成熟了
“你千万不要挂掉啊!”温雄珍抚摸着自己捡来的流浪猫,一边替它包扎伤口,一边反复叮嘱。
温雄珍不是一个擅长告别的人。1975年,她出生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家庭,在四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11岁那年,母亲病逝,家里东拼西凑,最后也只是让她多念了一年的书。
那天,她和父亲在菜地里拔着杂草。父亲低声问了句:“要么,我们不读书了吧?”温雄珍看不清父亲的眼神,但她从父亲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丝愧疚。
温雄珍是家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母亲似乎把未来的期望都寄托在她身上。小时候,母亲找人算过命,说如果她能读书的话,“以后会是不得了的人”。从此,母亲舍不得穿好的衣服,说要留给她上初中的时候穿。
在温雄珍的记忆里,家里的生活太苦了。父母从信用社贷款,养鸡,鸡发瘟;养猪,猪也发瘟。后来,母亲种了一园子的橘子树。结果,别人家种了三五年就挂果,她家的树却一直没有动静。
然而,就在母亲走的那年,整个园子忽然开满了花,挂满了果。那一刻,年幼的她觉得,命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1990年,15岁的温雄珍坐上了去广东南海的大巴,成了一名“厂妹”。她在布料厂打工,压花的机器温度很高,手指盖常被压到变形。她不敢在给父亲的信里写这些,只想着多赚点钱。
她记得很清楚,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05块钱,她把100块寄给了家里。在当时,这笔钱在老家足够给整个村子买下一个季度的肥料。
流水线之外的时间,温雄珍常常用来读诗、写诗。厂里其他工人发了工资会去买新衣服,唯独温雄珍却是一头扎进书店。她爱看武侠、科幻小说,还迷上了席慕蓉的诗。
她把情窦初开时的纠结写进了诗歌《如果》,尝试着给几个杂志社投稿。没想到,在小卖部的邮箱旁蹲守了一个月后,她真的收到了一本刊载着自己诗作的《江门文艺》。
“父亲拿着我的作品,到处跟人炫耀:你看,我的女儿会写诗!”每每回忆起已经离世的父亲,温雄珍时常会想到这一幕。
很多年后,在台风“蝴蝶”来袭之时,她看到一位卖菜的老人为了节省2块钱的摊位费,一直淋着大雨守在菜市场门口摆摊。她觉得,那位老人小心翼翼护着菜的样子,像极了自己的父亲,忍不住为他写了首诗。
2025年7月,温雄珍来到北京,成了鲁迅文学院作家研修班的一名学员。久违的校园生活,让她无比珍惜。上课、学习、读书,她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她时不时会收到同学们发来的照片,都是大家在校园里偶遇她看书时的场景。
“果子熟了,我又在上学了。”温雄珍轻声呢喃,仿佛父母又回到了身边。
生存
一箱杂志,还是一袋番薯?
1999年,温雄珍跟着丈夫到东莞企石镇摆摊卖鞋。他不爱看书,但知道温雄珍喜欢。有一回,他从上大学的侄子家里搬了一箱《读者》杂志给她。
“我兴奋地告诉一起摆摊的朋友,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结果他们不理解,说带书还不如带一袋番薯来吃咧!”温雄珍记得很多个这样的瞬间,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她投入文学的怀抱。
2003年初,“奇怪”的命运再次降临。春节前夕,温雄珍的丈夫在拉货途中遭遇车祸,被诊断为小腿粉碎性骨折,需要转院做手术。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温雄珍慌了神,面对昂贵的医药费和卧床静养的丈夫,她知道,自己必须撑起这个家。
那时,她拉着4岁大的女儿,抱着4个月大的儿子,继续出摊。“大年二十八那天生意特别好,孩子在一旁哭闹,有位顾客问我,为什么不叫老公来帮忙呢?我一听,眼泪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5年之久。温雄珍每天早上五六点出摊,晚上七八点回家,给孩子做饭、洗澡,一直忙到深夜。有天晚上11点多,堂弟打来电话。聊着聊着,他突然问道:“姐,你现在还写诗吗?”
她当场愣了一下:“日子过得这么苦,还怎么有心情写诗?”
但就在那一晚,她思索许久,还是动笔写下几行字:“生活有时是一首快乐的歌谣/有时是一副沉重的担子/生活再沉重,我也不能把你放下/如果生活只剩下轻盈,那么日后我便失去可炫耀的谈资。”
她又重新拾起书本。有一回,在摊位上,她一边给儿子喂奶,一边翻看《红与黑》,刚好被一个熟人的儿子撞见。他疑惑地问她:“你看得懂《红与黑》?我还以为你们只能看懂《家庭医生》呢。”
她只是淡淡地答了一句:“能看懂。”
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温雄珍也坚持要让孩子完成学业。2017年,大女儿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她像当年父亲炫耀她发表诗歌一样,在朋友圈“大肆宣传”。那阵子,整个市场的摊主们和熟客们都赶来祝贺她,她感到无比骄傲。
记录
每个字都会呼喊、会尖叫
后来,温雄珍在市场侧门租下了一个店面卖童装。虽然名为童装店,但其实从婴儿到成人的衣服、鞋子,甚至一些日用品都卖,不到10平方米的店面被塞得满满当当。
4年前,童装店生意不好,为了补贴孩子们的生活费,温雄珍每天下午4点半关店,随后匆忙赶去附近的一家烧烤店做兼职。
这是一对年轻夫妇开的烧烤店,主打湛江生蚝,室内室外摆着近十张桌子。温雄珍的工作是打扫卫生,给食材刷酱料,帮客人点菜、打包,有时还要送外卖。她一直戴着一副紫红色边框的近视眼镜,经常眯着眼查看外卖单子上的备注,生怕出错。
夜幕降临,烧烤店迎来人流高峰期,加上外卖订单扎堆,温雄珍愈发忙碌。偶尔她会和外卖员发生误会,或是给后厨下错指令,这些“小插曲”和对顾客的观察,都被她写进了诗中。
老板简观贵管她叫珍姐。起初他不知道她写诗,只觉得她干活利索,为人真诚。直到前两年,有记者过来采访、拍摄,还有顾客找她签名,他这才知道,原来珍姐还是一位诗人。
看着温雄珍的诗集《在炭火上安居》,简观贵若有所思。他说:“珍姐应该是想写我们普通人奋斗的内心世界。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一万小时定律’,珍姐一定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而对温雄珍来说,留意身边的人和事,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她把来到广东以后遇到的温暖的人和事,都写进了即将出版的诗集《东江水暖》中。最近,她还在读范雨素的《久别重逢》《劳动者的星辰》,她也想写写母亲、奶奶的故事,还有家乡的甘蔗地,以及她所看见的“人世间”。
“我记得刘亮程老师说过,要把自己的家乡和经历放到最后来写,那是最宝贵的财富。”温雄珍笑着说。
她觉得,自己正处于最好的创作阶段。有时重新翻看年轻时候的作品,她直言“好像有点幼稚”。“那时候没有贴近生活,如果一首作品离开了生活,它就是没有灵魂、没有血肉的。一个很简单的字,只要它有灵魂,都是会呼喊的、会尖叫的。”
如果没来广东,还会成为诗人吗?对于这个问题,她想了想,说:“可能会写诗,但不会被大家看到。”
专家点评
欧阳江河(著名诗人、诗学和文化评论家):
所有的人都可以跟诗有关
一个生活中的温雄珍,成为一个写作中的温雄珍,这是素人写作的一个最高成就。所有的人都可以跟诗有关,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AI怎么发展,只要人还有“心灵”这个根本的概念在,就会有诗歌。
刘颋(《文艺报》主编):
目光所到之处,就是诗歌生长之处
温雄珍的诗歌,让我们看到的是,她的目光所到之处,就是她的诗歌生长之处。比如说,她可以写身边的清洁女工,写烧烤架,也可以写加沙的难民。她的目光是面向生活、面向这个世界的,她关注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和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在这个意义上说,温雄珍的诗歌写作超越了,或者说正在定义我们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以及素人写作未来的方向。
不管是什么样的写作者,首先需要大家去认真、仔细、真诚地阅读其作品,而不是带着预设立场,甚至带着猎奇的眼光,从其身份入手去看待他们的写作。
卢辉(诗人、诗评家,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诗歌想象与经验的完美组合
读温雄珍的诗,总有一种幻觉在牵引着我们。这种幻觉既有神话的成分,又有信仰的成分;既有想象的成分,又有经验的成分。这几种成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温雄珍诗歌里想象的经验与经验的想象的完美组合。说到温雄珍诗歌里的经验的想象,我以为,经验可以是经历过的,也可以是正在经历着的。因此,经验既可“现身”表达,也可以“想象”抒写,而诗歌就是其中制造经验的想象模式。
胡磊(东莞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
温雄珍的诗歌具有天然的底层生活质感
温雄珍的诗歌无疑具有天然的底层生活的质感,她驾轻就熟地选择草根的视角和平民立场,依凭感同身受的底层经历表达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和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她与她关注的对象构成一种伦理关系,她诗歌中的意象和她经历的生活一样鲜活。对她笔下那些游走于生活边缘的底层人群,如乞讨的老女人、扫地的阿姨、守护茶园的老张,她在字里行间表达岀相互理解的可能,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同时指呈他们精神上的孤独困境。
往期阅读:
采写/出镜:南方+记者 黄堃媛
脚本:南方+记者 黄堃媛 赵媛媛
摄影/摄像:南方+记者 仇敏业 姚志豪
剪辑:南方+记者 陈文夏
海报设计:程子宜
统筹:李贺 李培 郭珊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