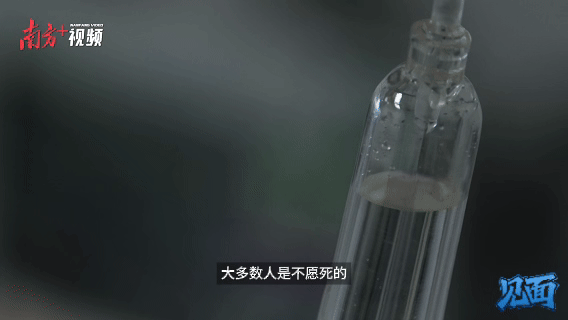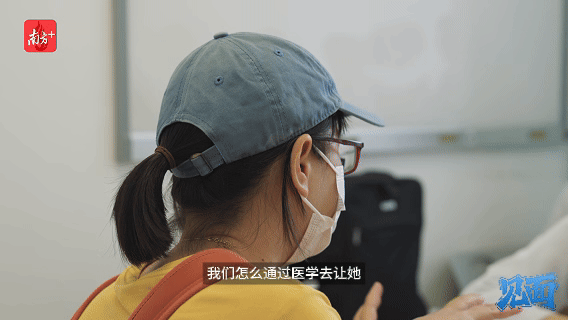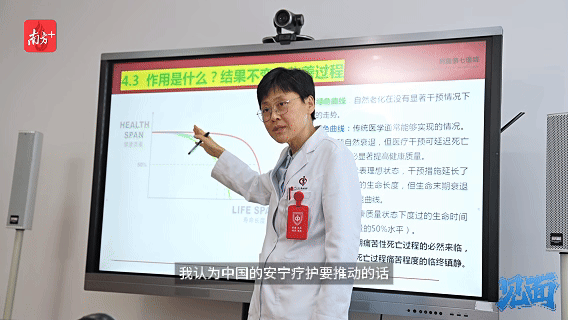![]() 07:02
07:02
![]()
![]()
生命落幕时,郭艳汝既医“生”又疗“别”
一个科室,一名医生,四张病床——这是郭艳汝最初的“家当”。
与大多数医生不同,她的工作,并非让患者延续生命,而是帮助他们体面告别。
“未知生,焉知死。”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现实,但当它真正来临时,多数人依然会感到不安与恐惧。
郭艳汝却十余年如一日,坚守在这条“冷门”的安宁疗护路上,用专业和陪伴让告别不再孤单。
10月11日是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中山大学第七附属医院二期工程施工现场“热气腾腾”,郭艳汝正筹设一处拥有20张床位的安宁疗护病区,希望帮助更多患者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01
一次挂号一小时问诊
在人声鼎沸的医院门诊楼,安宁疗护门诊没有拥挤的人群,显得格外安静。
菀柔戴着口罩走进诊室,一看到郭艳汝,情绪倾泻而出:“我们不想让妈妈再受苦了,希望她能走得舒服些。”
菀柔母亲正处于肺癌晚期,胸腔积液严重,消瘦得不成样子。目睹母亲在治疗中承受的痛苦,菀柔既无奈又心痛。她和家人郑重召开了家庭会议,基本同意不再让母亲接受过度治疗,但在作出最终决定前,还要慎重地听听医生的专业意见。
安宁疗护,是为终末期或老年患者提供身体、心理、社会和精神多维度的照护,帮助他们减轻痛苦,用一种更安适、更有尊严的方式离世,以提升生命“最后一公里”的质量。
“您说妈妈性格比较悲观,能不能具体说一两件事?”面对菀柔的疑问,郭艳汝没有急着作答,而是让她先讲清楚母亲的生活习惯、病情以及未尽心愿。
菀柔沉默片刻,缓缓开口:“她童年很苦,父亲早逝。年纪大了才嫁给我父亲,一手养大5个孩子,真的很辛苦。”
郭艳汝点点头,追问:“她有没有跟你们说过自己的想法?比如,不进ICU,不插管?”
“有的。”菀柔湿了眼眶,说:“她说过不要插管,不要抢救。只想吃得下饭,睡得着觉,排便通畅,不要太痛苦。”
郭艳汝轻声说:“这是她在临终前的医疗选择。很多子女替老人决定,而你们把选择权留给她,这很重要……”
一个小时的对话里,郭艳汝边倾听,边手绘图解:药物如何选择、线上复诊如何操作、居家安宁疗护注意事项……但鲜有人知道,这样一小时的问诊,挂号费只有33元。
医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有人把医生的救治等同于“起死回生”,把治愈视为唯一目标。但当生命走到尽头,医学技术究竟是让人“好好活着”,还是延长痛苦地离去?
“最重要的是尊重患者的真实意愿。”郭艳汝说。
对一名医生来说,33元诊金,一个小时问诊,是否值得?郭艳汝快言快语:只要能让患者知道,除了进ICU、反复抢救或回家等死,还有安宁疗护这条中间路,少一些事后懊悔,那就值得。
02
生命有尊严谢幕要更早准备
每天,郭艳汝都在直面死亡的冲击。
第一次冲击,发生在大学毕业前实习的肿瘤医院,她至今记忆深刻。在肿瘤医院门口,一位胰腺癌晚期患者留下遗书:“我不是来治病的,我是来止疼的。难道止疼,不是医疗价值吗?”
当治愈已无可能,医学还能做什么?
当死亡不可避免,医生的价值又在哪里?
在传统观念中,抢救成功、延长生命、治愈疾病,才算“有价值”。时间流逝,这两个问题始终萦绕在郭艳汝心头。
2010年,郭艳汝所在的河北沧州一家医院筹建疼痛门诊,她进修归来后接手开诊。这一被视为“冷门”的岗位,却成了一大批无法再化疗、住不进病房的生命末期患者的“避风港”。他们依靠止痛药缓解疼痛,有尊严地完成了生命的谢幕。
最初,不少家属并不信任郭艳汝,坚持要求“照旧开药”。她没有妥协,坚持先了解病情再开方。
随着患者疼痛缓解、家属释然,郭艳汝逐渐积累经验,也愈发明白:医学的难点,不在药物,而在家庭、情感与医学原则之间做权衡。
6年前,在医院的支持下,郭艳汝创建了安宁疗护科,担任科室主任。那时,她对“善终”的理解正逐渐清晰——
死亡并非医学的敌人,而是生命必然的一部分。当治愈已无可能时,医生的价值就是帮助患者走完最后一程。
89岁的瑞祥,年轻时意气风发,晚年却丧失40多岁的爱子。此后他把孙子抚养长大,成为生命中唯一的牵挂。
确诊肿瘤后,瑞祥住进郭艳汝的病房。第二天,他便提出办理财产公证,将名下所有留给孙子。
几天后,他对郭艳汝说:“我现在半碗小米粥都喝不下去了,咱俩该聊聊医疗的事情了。”
他语气平和地交代——不要插管,不进ICU,不做心肺复苏;等到再也吃不下东西、犯迷糊时,把输液管也拔了。
一条条要求,让瑞祥的孙子愣住了。他本能怀疑:不再用药输液,不是等于“饿死”爷爷吗?
虽然郭艳汝理解老人的选择,但她也在想,怎么跟家属说,才能让他们听得懂、也能接受患者的决定。
为了拨开迷雾,她开始坚持一周读一本书,阅读范围跨越医学、伦理学、哲学、逻辑学、法学,甚至中国医改史。她反复查阅文献、翻看法律条文,力求从更全面的视角理解“人临终时最真实的需求”。
瑞祥离世后,留给郭艳汝一封信,信里写道:“我一生经历了太多不幸。你问我是否有遗憾?当然有。但人这一辈子,就是要学会接受遗憾。那边有许多亲人在等着我,我可以安心地走了。”
郭艳汝常常想起信中最后一句:“该做的事都做了,至于结果,不必强求。”
那一刻,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死亡是人生最后一程,但并不是终点。
如今,谈及安宁疗护时,不少人仍倾向于理想化,强调“带着尊严谢幕”。而郭艳汝的体会更为朴素:死亡本身是痛苦和残酷的,单靠安宁疗护无法让它完全“有尊严”。
“真正的尊严,是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患者更早按照自己心愿去活,是有机会把重要的事和人交代清楚。而这些,仅靠生命最后几天的安宁疗护远远不够。”她说。
一次学术会交流上,有位老教授惊讶于她的见解,问:“你是不是留过学?”
郭艳汝笑着答:“没有,我就是自学的。”
03
把选择权交到患者家属手里
在安宁疗护诊室,7位来自广东不同医院的进修护士围坐一圈,桌上摊开一份安宁疗护病历。
郭艳汝环顾众人,语气平静却直抵人心:“患者走到生命终点,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和家人一起面对死亡?”
空气顿时凝重起来。有人建议从日常生活聊起,有人主张直接询问患者最在意的事情,还有人认为要先安抚家属情绪。
那一刻,这不仅是一场病例讨论,更像是一堂关于生命的课——教人如何倾听、如何告别。
传统的家庭文化中,生命末期的患者往往难以独自作出决定。即使意识清醒,他们也常把生死的抉择“让渡”给子女或亲人。
这看似合情合理,做起来却极为艰难——患者的意愿与家庭的意见纠缠交错,常常成为一场拉锯战。郭艳汝常常要在劝慰与尊重之间反复权衡。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52岁的阿霞因胃癌晚期住进中山七院,预期生存期仅两个月。她的出现,成了那段时间郭艳汝最放不下的牵挂。
阿霞始终放不下两个尚未成家的孩子,一心想坚持治疗。她的妹妹是一名护士,更是态度坚决:“哪怕撑到年底,也要化疗!”
现实很快击穿希望。阿霞病情加重,家属不断推翻治疗方案,让管床医生陷入两难。
郭艳汝没有急着劝说,而是先为阿霞做好基础症状控制,再用解释与陪伴一点点建立信任。“不希望她走得太痛。但在患者没准备好、家庭还未达成共识之前,谈‘放手’没有意义。”她说。
这份耐心沟通的“定力”,源于她早年在沧州从事安宁疗护的经历。
有一次,一名黑色素瘤患者因回家途中堵车,最终在救护车上离世,没能如愿在家中咽气。
家属悲痛交加,怒气冲冲闯进科室,情绪几近失控。
眼看同事可能遭到殴打,郭艳汝下意识扑上前,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低声劝说:“真想发泄,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这里人多,被录下来不好。”
看着语气诚恳、身材消瘦的郭艳汝,家属愣了几秒,最终放下了拳头。
“其实,我是一个‘怂人’。”她说,遇到可能发生的暴力,她也会心虚、害怕。但在那一刻,她必须硬着头皮站出来。
“患者在世时,医生、患者和家属三方关系能维持平衡。可一旦患者离世,家属的情绪往往需要一个发泄出口。”郭艳汝冷静地说,作为医生,要履行好告知的义务,但如何决定,终究是患者和家属的权利。
04
让更多人“好好告别”
几年前,郭艳汝在互联网上开讲安宁疗护,意外成为“网红医生”。
谈及“触网”的初衷,她笑着说:“只是想让更多人认识生命,理解死亡。”
几年间,她逐步探索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服务模式,设立独立科室,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打通基层转介网络。
“能力、理解都到了位,再做就是重复。”她坦言,若想推动安宁疗护成为真正的普惠性公共服务,仅靠单点探索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强的制度支撑与政策辐射力。
一年前,郭艳汝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南下深圳,成为中山七院安宁疗护科第一位专职从事安宁疗护的医生。一年来,她几乎没有停下脚步——
在医院,她推动建立安宁疗护会诊机制和院内“共照模式”,让全院任何一张病床都能获得安宁疗护服务;同时开设安宁门诊,开通线上咨询通道,让患者少些等待与奔波;
在深圳,她借助较为成熟的医保政策,推动多家医院床位互通、信息共享;
在广东,她参与制定全国首部省级安宁疗护服务项目指南,对症状评估、生存期评估等13项服务项目及内容进行细化和规范……
即便如此,她依然常常被生命末期患者触动。
——那些临终前的呼吸、犹豫、告别,提醒她这条路还很长。
查出脑胶质瘤时,鹏鹏才15岁。父母年近半百,为了孩子几乎跑遍广州的大医院,只为抓住一丝希望。面对多次“建议放弃”的评估,他们无奈将孩子接回深圳,在ICU里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长时间的维持治疗让鹏鹏的身体出现压疮、皮肤破溃,关节畸形,四肢僵硬弯曲,穿一次衣服都需要多人协助。
鹏鹏妈妈多次与郭艳汝约定拔管,却每次都在最后一刻“反悔”。因为一旦拔管,死亡就近在咫尺。
这场“不能承受之重”,鹏鹏妈妈拖了整整一个多月,直到某天她看见儿子脚踝溃烂,才终于咬牙作出决定。
送别当天,鹏鹏妈妈一遍遍对医护人员说“谢谢”。一句句“谢谢”就像一种情绪寄托,也是一种自我修复的开始。
对患者来说,死亡不是抽象的哲学命题,而是一场真实而漫长的告别。安宁疗护,就是陪他们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今年7月,广东出台《广东省安宁疗护服务项目指南》。在郭艳汝看来,这一指南的突破点在于把人当成完整的个体,既关注身体症状,也关注生命末期的心理、社会和情感需求,并引导家属倾听患者真正的心愿,而非单方面决定治疗方案。
医学有边界,并非万能。“医者不是神,救不了所有人。但如果能陪患者把最后一段路走得舒适、体面、尊严一点,就已经很好了。”郭艳汝轻声说。
医者仁心,不止于“治愈”,更在于“善终”;既医“生”,亦医“死”。
(文中菀柔、瑞祥、阿霞、鹏鹏均为化名)
采写:南方+记者 厉思璇 吴少敏 张梓望
编导/摄影:南方+记者 张梓望 许舒智 厉思璇
剪辑:卓杰
海报:甘展平
统筹:吴少敏 张西陆 丁晓然 刘子葵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