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暑期档(6月1日—8月31日)佳作迭出、市场火热,截至发稿总票房已超70亿元。本期文艺评论特邀上海知名影评人点评粤产电影《长安的荔枝》,及广东影视专家点评上海影企参与制作、出品的电影《南京照相馆》,分析如何在大银幕上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展现地方人文形象。
《长安的荔枝》:岭南文化的血性与柔情 | 沪粤文艺对话
王培雷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家喻户晓的古诗名句,钩沉起大唐由盛转衰之际的冰山一角。无论是杜牧的《过华清宫》,还是清代剧作家洪昇的《长生殿》,都将“岭南荔枝进长安”加以具象化,成为对“江山美人”的一种指涉与讽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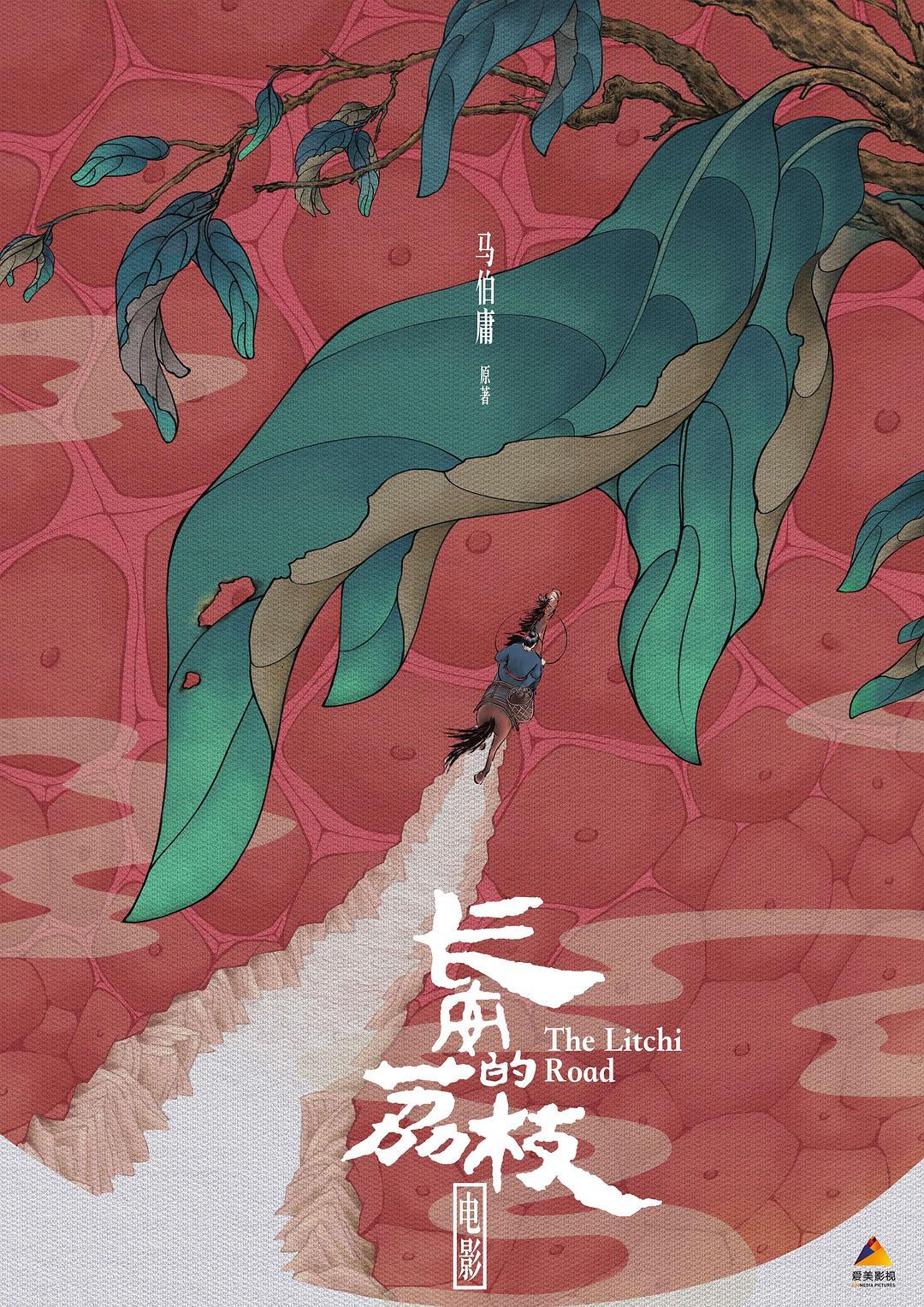
电影《长安的荔枝》概念海报。
近年来,在许多戏曲、文学、影视作品中,“一骑红尘”的故事往往被简化为“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旷世之恋”。马伯庸的小说《长安的荔枝》却对这个主题作了当代化处理,专注于底层官吏李善德从岭南极限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的任务,带出一整个古代“官场现形记”。大鹏导演的电影版,携2023年末他主演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之余波,再现大唐“打工人”反抗不公命运,而唐明皇与贵妃的形象被虚化为背景。至此,“无人知是荔枝来”已从最初的针砭时弊,蜕变为关乎个人命运与身处环境的深刻寓言。
这部时长两个多小时的电影版,延续了大鹏导演一以贯之的风格,既在商业类型架构中注入洞悉世事的幽默感,又在叙事行进中充分赋予角色以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既为导演自身的作品序列增添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亦在中国电影商业片探索上提供了相当可贵的思路。
影片以李善德(大鹏饰)的第一人称旁白展开叙事,从一开始就道出了主人公作为正直的底层官员遭同僚排挤、被上司算计的不公处境。影片通过精准、高效的镜头语言,接力赛一般描绘了奸诈的上司、狡猾的宦官鱼朝恩、充满现代女性气质的李夫人郑玉婷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观众很容易被带进类似《年会不能停!》的叙事期待:李善德如何战胜艰难险阻完成任务?能否开启“整顿职场”的“爽剧”模式?而这种期待也成为影片的核心叙事推动力。

电影《长安的荔枝》海报。
无论是马伯庸的小说还是电影的呈现,都将彼时岭南与长安的地理距离与运输方式作为叙事张力之一环。李善德在规定期限内,不断根据广东地理特点、荔枝成长周期及各种当时可行的保鲜方式及交通条件,反复进行推演、优化,并最终亲身上阵护送荔枝返京。这一系列过程,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之旅”裹挟在人物不断逆袭的命运之中,伴随着李善德在岭南的具体见闻及其与商人苏谅之间的友情,影片叙事中承载的人文地理与历史细节也不断得以丰富,令“传送荔枝”的动作于扣人心弦之外,更引发观众对“意在言外”的深层思考。
而这正是《长安的荔枝》所欲达成的言志之处——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李善德甚至如伍子胥一般“一夜白头”,他冲破重重障碍,终于将荔枝送到贵妃面前,角色的弧光至此已经悲壮地完整了。然而,荔枝在贵妃手指间只是轻轻一触,与满桌奇珍异果一道,顿时化为“盛唐危机”的缩影。

电影《长安的荔枝》拍摄现场。
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之外,《长安的荔枝》也没有忽略对组成历史的具体的人与时代样貌的还原,尤其是对岭南风物的书写。透过对荔枝的种植、采摘、历史渊源、成长环境及运输技术等全方位的展示,影片让习惯了一切生活便利的今人得以直观感知杜牧诗句中的原初语境,以及昔日的普罗众生是如何千辛万苦地推动历史进程的。在以阿僮为代表的荔农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勉、智慧的传统美德,更彰显出岭南人的血性与柔情。李善德最后远离朝廷纷争、退隐岭南,亦是这种“可进可退”的文化个性的艺术化再现。放大了看,岭南文化中的奋发有为、英雄意气与宽广胸怀,甚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是全球华人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脉。
无独有偶,同期上映的《南京照相馆》深度刻画了生死关头南京城里的人民的心灵选择,以及南京以怎样的姿态包容并激励了来自不同故乡的主人公奋起抗争,在展现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上,与《长安的荔枝》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文化旨趣,有望成为未来探索和塑造中国电影美学的重要议题。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讲师,上海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博士)
《南京照相馆》:“镜”与“枪”之喻
涂俊仪
《南京照相馆》以“照相”巧妙结构起故事内容,在如何书写暴行与苦难、如何书写战争中的人、如何用好物的隐喻等几方面展现出新颖独到之处。电影作为南京大屠杀题材影视作品中的新作,在暑期档票房困境中强势突围,观影人次快速上涨,受到了当下观众的普遍认可。

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
对于南京大屠杀中这份沉重的历史记忆,电影采用了较为内敛的笔触,避免过度的戏剧化与煽情。影片很少直接描绘暴行,而多以景深镜头进行视觉语言处理,在前景人物的互动或惊恐之间,后景已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径。故事在时间线上保持着与现实时间的同步,这种“冷处理”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杀人施暴对侵略者来说有如饮食一般寻常,更凸显了其冷酷与残忍。电影在情感表达上同样是克制的,剧情虽以苏柳昌与伊藤秀夫两条行动线索推进,但叙事上主要采用全知视角,避免单一人物视角过度影响乃至支配观影时的价值判断,充分显示出对观众的尊重。
如何书写战争中的“人”,则是战争题材作品的另一重要功课。影片中的“我”并非只是大屠杀中的个体受难者,还象征着无数中国人民,是观众自我认同的投射对象。在一开始的设定中,温良就是人物的性格底色。电影并没有过多着墨于描绘照相馆主角群像的人性心理,而是重点描写人物对战争的认知变化以及由此激发的民族精神:林毓秀在亲历日本人的穷凶极恶后不再心存幻想,举出穆桂英、梁红玉等例子对王广海发出质问;宋存义在见过弟弟被残忍杀害的照片之后,以日本军人池田为目标伺机报复;金承宗在照相馆里展现“日行千里”的祖国风光,众人在泪光闪烁之中发出“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呐喊……这些情感爆发点,都不在于描述个体的悲欢,而在于表现家国大义及流动于中国人血液中守土卫疆的精神。

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
另外,影片不单揭露了侵华日军的丑陋和残忍,更对群体之恶有着深刻的洞察与交代。伊藤秀夫一开始展现出怯懦与不安,与诸多凶狠残暴的军人形成了反差。他多次被上司教唆杀人,却迟迟不敢下手。最终,当伊藤秀夫半边脸被酸水腐蚀,在火光之中如同恶魔一般咆哮,并刺杀了其称为“朋友”的苏柳昌时,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昭然若揭。但电影并没有将伊藤秀夫塑造为单纯的战争受害者,包括他给苏柳昌写“安全证明”时加上“两日之内”,对自己的胶片视如珍宝却说“中国人的照片不重要”,提及其爷爷参与甲午战争时“惋惜”没能攻下北京等,一切都表明角色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荼毒,为后续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照相机是记录工具,是艺术媒介,还可以是制造假象的凶器。伊藤秀夫在进入千疮百孔的南京之前,其手中的照相机曾拍摄过中国的锦绣山河。在大屠杀中,他的镜头对准无数暴行的现场,夸耀侵略者的淫威,及至在拍摄虚伪的“中日亲善照”时,让相机成为助纣为虐的侵略战争宣传工具。相机在伊藤手中作用的转变,叠合了伊藤的多重形象。英文“shoot”一词,包括“拍摄”和“开枪”两个意思。伊藤虽怯于执枪,却通过照相机对受害者实施侵犯与虐待。剧终,林毓秀手执相机拍摄下日本战犯被枪决的一幕,拍摄与被拍摄的位置转换,意味着将控诉侵略者、向全世界讲述这段历史的权利紧紧握在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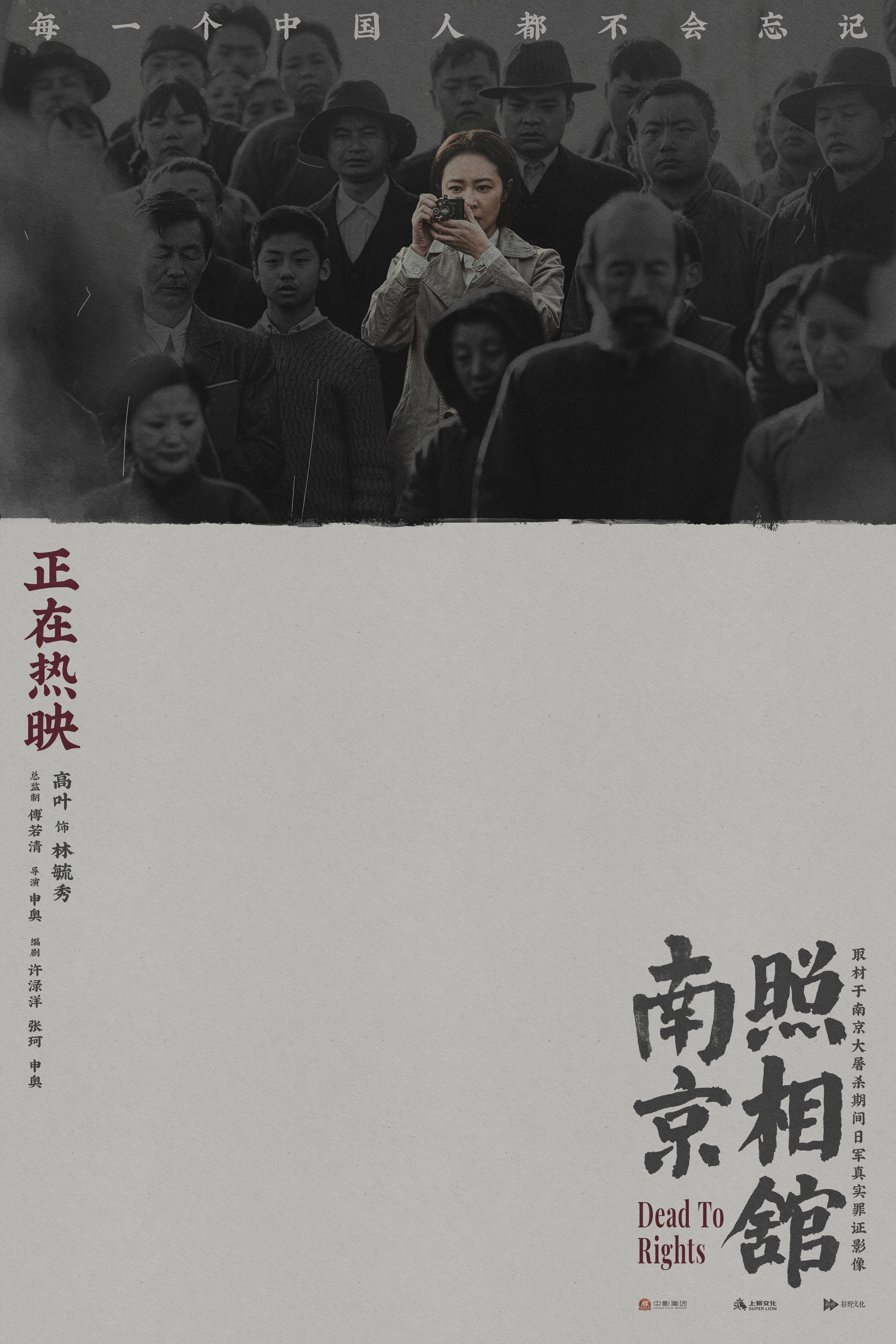
电影《南京照相馆》海报。
对于一部重大历史题材影片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还有讲述故事的年代。只有抓住受众的社会心理与人心所向,才能引发广泛的共鸣。宋存义在艰难的搏斗中,用城墙砖块给予池田致命一击,以“快意恩仇”呼应了银幕外观众的期待。这抵抗之力,正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一帧写照。不同于《南京!南京!》描述日本士兵的恻隐之心与悔罪自杀,《金陵十三钗》寄希望于第三方施以援手,《南京照相馆》展现的是人物在夹缝中辗转求生,并以底片作为还击侵略者的有力武器,在结尾处更直接呈现了对侵华日军战犯的审判和枪决。
文艺作品对历史记忆的叩访与再述,关乎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和判断。如同林毓秀夺回了执掌照相机的权利,光影世界对民族集体记忆的艺术再现,在打破时空隔阂的同时,也赋予了其更具有当下意义的价值判断与反思。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