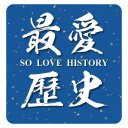当黄道婆登上返乡的海船,她也许未曾料到,此行将会给乌泥泾镇带来一场巨变。
相传,早年身为童养媳的黄道婆因不堪夫家欺凌,乘船逃往崖州(今海南三亚),一住就是三十年。崖州土著素来有种棉织布的传统,黄道婆很快就被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折服,虚心求教,逐渐习得一套领先中原的棉纺织技术。
到了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黄道婆乘船返回故乡——松江府乌泥泾镇后,无以为靠,只得“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
当时,乌泥泾镇一带因“地土硗瘠,民食不给”,百姓便因地制宜改种棉花,但苦于技术无有突破,棉布产量难以增加。见此情景,黄道婆将从崖州学到的棉纺织技术加以改进,向众人倾囊相授。一时间,“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在黄道婆的技术加持下,当地人逐渐逆袭,实现了家给人足。
高峰时,一镇就有千余户从事棉纺织业,乌泥泾镇的经济结构因此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受此带动,松江府的棉作超越了稻作,逐渐成为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重镇,并随之有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美誉。
▲江南古镇。图源:摄图网授权
在普遍重农抑商的传统帝制时代,以乌泥泾镇为代表的江南市镇,却渐渐脱离传统的粮食生产,走出了一条别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追溯江南市镇的起点,绕不开宋代的军镇转型与草市兴起。
通常认为,军镇的建制始于北魏。北魏朝廷为应对北境军事压力,“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随着军队的长期屯驻,贩夫走卒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加之军镇往往设置于水陆交通的要冲之地,商贸活动愈发繁盛。以边防为重心的军镇,由此带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中唐安史之乱后,内地亦开始增设军镇,分戍地方。此后,各地军镇与商业之间的互动持续进行,军镇的军事功能慢慢弱化。
北宋建立后,出于对军事政变和武人政治的担忧,赵氏在中央“杯酒释兵权”,在地方则“诸镇省罢略尽”,将藩镇权悉数收归朝廷,以此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各军镇失去军事意义后,商业活动却未一同消亡。对于这些小型商埠,朝廷直接入场接管,“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监官,管火禁或兼酒税之事”。
与依附于军队发展起来的商镇相比,草市则更依赖于城市和乡村。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市已经出现。最初的草市,是指在官方设立州县坊市之外的一种非正规交易场所,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服务于小农、调剂余缺的小型乡村集市。唐代对商业活动有着“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的明文限制,草市就在这种不被官府认可的情况下缓慢发展。转机与变革,同样出现在了宋代。
北宋建立后,经济重焕生机。史载,“景德、祥符间,斯民富且庶矣。当是之时,人人乐业,庐里之中,鼓乐之音,远近相闻,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经济恢复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使得城市愈发拥挤,剩余人口不得不散出城外居住,城厢制度应运而生。然而,城内原有的坊市,并不能满足城厢居民的消费需求。于是,一批“附城草市”随之兴起,为城墙以外的城厢居民提供各种消费品。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汴梁(今河南开封)郊外的草市已极具规模,达到了“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的地步。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回忆,当时汴梁城郊已经出现了都市农业,“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
▲北宋《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草市的兴起不可逆,北宋坦然接受了这一现实。宋真宗时期,朝廷开始对各地草市征收商税。到了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全国又掀起“草市升镇”的浪潮。至此,起初不被认可的草市终于完成了身份跃迁,走到历史的前台。
无论是军镇,亦或是草市,随着镇官与税务官的到任,这些新兴市镇正式被纳入北宋的行政体系中。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宋代是中国市镇发展史上的转捩点,正是从这时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从超大型城市的形成转向中小城镇的起步。
相较于中原市镇,江南市镇的兴起,则多了一些“意外”的因素。
靖康之变后,包括北宋皇族在内,大批中原人士南下避祸,这场人口大迁移后来被称为“建炎南渡”。对于中原而言,这是一场灾难;可对于江南,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南宋政权的建立,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乌鸦变凤凰,地位直逼北宋旧都汴梁。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临安人口暴增,汴梁旧景再现——城市剩余人口大量外溢,大批附郭市镇兴起。南宋笔记《都城纪胜》记录了临安城外的这一盛况:
“今中兴行都已百余年,其户口蕃息仅(近)百万余家者。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
▲浙江杭州塘栖古镇。图源:摄图网授权
在建炎南渡中,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江南迎来了自吴越、南唐之后的又一次大发展。移民来到江南后,在南宋朝廷的招抚下,分田务农或编入军队。但仍有不少人为谋生计而投身于商贾之列,江南草市、商镇逐渐兴起,以至于在常州辖下的晋陵、武进两县出现了“诸关城外皆有小市”的繁荣景象。
对于江南市镇的兴起,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因能从中获得巨额商税,故亦乐见其成。而在此之前,朝廷需要在这些新兴市镇中设立镇官与税务官,为其正名。得到朝廷认可后,江南市镇快速发展。比如,南宋中期,海盐县澉浦因“专通番舶”成为坐拥五千户的江南大镇,时人称其“人物繁阜,不啻汉一大县”。
但此时,江南市镇的功能仍旧十分传统,主要是为周边城乡居民提供日常消费物资,“布粟蔬薪之外,更无长物”。两宋的舞台,显然已经有些局促了。
十三世纪中后期,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下走向崩溃,终为元朝取代。不同于以往的中原政权,元朝多数时间里重农不抑商,对江南实行的是几近于自由放纵的经济统治政策。一个农商并重的大一统政权,对于江南市镇的发展,无疑是利好的。
元朝对科举不甚重视,一度停考长达数十年。许多读书人无奈接受这一现实,开始转投于商业活动。久而久之,弃文从商蔚然成风,江南社会“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即便是一些官宦之家,也不乏弃官从商之人。
无锡人徐元度,“起家儒林”,是科举制的拥趸。在元廷任职期间,是公认的好官。然而,官场生涯并未给他带来物质层面的富足,反倒是“身显而家益贫”。徐元度的政治地位与经济收入严重不对等的状况,给儿子徐仲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后,徐仲刚完全没有入仕的热情,转而经营家业,“田畴之荒者治之,室屋之敝者葺之”,最终带领家族实现了生活的富足。
一些原本在仕途上有着大好前程之人,也纷纷“下海”。如金陵人李汝成,果断放弃仕进,“贾六合市上”;左丞相阿里海牙之孙贯云石,原本享受着翰林学士的高位,亦毅然放弃官爵,在江南的钱塘隐姓埋名,“卖药市肆”,当起了药材商人。
元朝从商的风气盛行后,“名士逸民,都无心于仕进,终元之世,江南登进士者,止十九人而已”。对于这一历史反常现象,晚明嘉兴人李日华解释道:“元季,士君子不乐仕,而法网宽,田赋三十税一,故野处者,得以赀雄,而乐其志如此。”重商而轻仕,实属帝制时代的一朵奇葩。这不仅影响到个人前程,也改变着江南市镇的走向。
浙江濮院镇原是江南一个普通的草市。南宋时期,濮凤携家带口移居此地,因其后人、吏部侍郎濮光斗为宋理宗所器重,濮氏家宅获赐名为濮院。此后,该草市在濮氏家族桑蚕丝织业的带动下走向繁盛,进而得名濮院镇。南宋灭亡后,元廷鼓励农商发展,濮氏家族遂在经营桑蚕丝织业的基础上,兼营丝绸集散贸易,又于大德十一年(1307)春,斥资万金设立了具有贸易中介性质的四大牙行,逐渐将濮院镇经营成为江南地区的丝绸重镇。
▲浙江桐乡濮院香海禅寺。图源:摄图网授权
海盐县澉浦镇是江南海运重镇,早在两宋时期,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元革宋鼎之后,元廷不但承袭了宋代市舶司制度,还将这一重要管理机构设置于澉浦镇。同时,元世祖忽必烈将庆元(今浙江宁波)与上海等另外两处市舶司一并交由熟悉海事的杨发家族打理。经过杨氏三代人的经营,澉浦一跃而成为与泉州、太仓齐名的海外贸易中心。
农商并重,同样促成江南棉业市镇的兴起。
起初,江南并非棉花的主场。作为外来经济物种,直到宋末元初,棉花才进入长江、黄河流域。当时,江南部分地区因土质问题,百姓不得已之下“因谋树艺,以资生业”,将棉花种植当成副业发展,用以填补粮产的不足。但,直到元朝涉棉政策与技术发生变化前,江南的棉花产业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忽必烈“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先后设立劝农司和司农司,督导各地农业生产,鼓励棉花种植。至元二十六年(1289)夏,元朝政府“置浙江、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采用行政手段推进江南地区的棉业生产。到了元贞二年(1296),元成宗又对江南税制进行改革,“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将棉布列为常赋之物。
同样在元贞年间(1295—1297),江南落后的棉纺织业因黄道婆“教以造捍弹纺织之具”,迎来了一轮技术革新。于是,在政策推动与技术革新所形成的奇妙合力之下,江南地区热烈拥抱这一新兴产业,并培育出以乌泥泾镇为代表的一批棉业市镇。
可以说,棉业市镇的出现,是元代江南市镇走向专业化的缩影。
与元代放纵江南自由发展不同,明初之于江南市镇,不亚于一场噩梦。
明初,朱元璋对江南实行抑豪刬富的国策,强令江南富民迁徙他处,一代传奇巨富沈万三及其家族也在这场移民运动中走向衰落。这一高压政策,几乎等同于釜底抽薪,使以富家巨室为基础的江南市镇陷入近百年的凋敝状态,甚至一度激起了民间追忆前朝盛况的“元季情结”。
尽管备受打击,但假以时日,江南市镇仍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到明代中期,人口激增,江南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严峻,剩余人口不得不转入尚未充分发展的商品贸易领域。自此以后,延至清代,江南市镇经济趋于专业化的特点愈发明显。
▲苏州山塘街。图源:摄图网授权
作为江南地区最为重要的两种货品,棉布和丝绸始终是难以绕开的话题。
继元朝于江南大力推广棉花后,明朝亦不遑多让。明初,朱元璋曾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仍对植棉念念不忘,再度下诏“(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授以种法,而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明末时期,江南的棉花种植已远超水稻,太仓地区“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
位于太仓的鹤王市,既是明代的优质棉花产地,也是重要的棉花集散市镇。鹤王市一带的棉花因“比之他乡,柔韧而加白”,声名远扬。每当棉商打出“太仓鹤王市棉花”的旗号,来自远方的闽广商人纷纷争相收购。靠着棉花产业,鹤王市每年秋季的交易额高达“数十万金”。
吴江县盛泽镇,是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丝织重镇。明初,盛泽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因人口稀少,甚至于“屠日不能毕一豚”。但到了嘉靖年间,重织轻耕、以绫绸为业的盛泽逐渐聚拢大量人口,升格成为市镇。关于盛泽镇的繁荣,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线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清代,盛泽镇的丝绸贸易依旧繁荣。当地贸易往往以“每日中为市”,高峰期的交易额甚至达到“日逾万金”的程度。
棉丝经济的兴盛,逐渐挤占了江南粮食作物的生产空间,部分地区形成“棉七稻三”的农业格局。南宋时期“苏湖熟,天下足”的景象,竟在明清时期成为了过眼云烟,江南地区不仅供应不了天下粮食,还严重依赖外粮输入。于是乎,一些主打粮食转运贸易的市镇也开始勃兴。
▲苏州枫桥古镇渔隐桥。图源:摄图网授权
枫桥镇,位于苏州城郊,毗邻京杭大运河。明清时期,因其交通区位优势明显,逐渐发展为江南地区最大的米粮转运中心,“各省商米豆麦,屯聚于此”。清代乾、嘉时期,枫桥镇粮食贸易达到高峰,镇中米行多达200余家。
除枫桥镇外,吴江县平望镇也是江南一大米粮集散中心。早在明朝初年,平望镇便已经是“居民千百家”的人口大镇。而且,当地“里中多以贩米为业”,粮米加工也极为发达。每当湖广等地的运粮船抵达,平望镇便呈现出一幅“千艘万舸,远近毕集”的画面,热闹之程度,可与枫桥镇相媲美。
自江南市镇兴起以来,每一次王朝更迭所带来的战乱,几乎都会变成一把扼杀的剑,轻则元气大伤,重则湮没消亡。
元明鼎革时期,嘉兴县濮院镇受到战火波及,备受打击。至正十七年(1357),元将杨完者领兵进驻该镇。一些地痞无赖闻讯,纷纷成为带路党。在这些人的指引下,杨完者“抄括院境,掳男女老幼皆杀之”,在濮院镇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作为江南的丝织业重镇,当地产业在这场灾难中受损严重,纺织工人“杳然散去者岁余”。事后,经过濮氏一族的努力,濮院镇方才“稍稍渐振”。
然而,好景不长。至正二十六年(1366),张士诚与朱元璋所部大战于嘉兴一带。濮氏家族见状,特意借粮给张士诚的女婿潘绍元,希望以此换取濮院镇的和平。怎料,张士诚大军后来为朱元璋所败,濮氏家族也因借粮行为得罪于朱元璋,遭到严厉清算。濮氏一族“三十七昆弟”被朱元璋强令拆分,迁徙他处。到了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朱棣发起了对靖难之役的清算,一些已经回归濮院镇的濮氏族人因与“建文遗臣”杨任有姻亲关系,不得不隐姓埋名,再度远遁他乡避祸。直到弘治、正德年间,濮氏家族及濮院镇才重新走向复兴。
在元末的战乱中,其他一些江南市镇也未能幸免于难。如乌青镇(今浙江桐乡市乌镇)“民庐寺观书馆举为煨烬矣,其仅存者唯两浮屠之遗迹焉”,全镇几近毁灭;璜泾镇因战乱波及,“民始荡析离居,而昔时繁华之地鞠为草莽之区矣”,破败不堪。战争对于江南市镇之害,由此可见一斑。
▲江南水乡:乌镇。图源:摄图网授权
除去战乱,江南市镇亦面临着其他纷繁复杂的危机与挑战。
上海县乌泥泾镇,曾是元朝带动松江府“衣被天下”的棉业重镇,一度“人民炽盛于他镇”。可到了明朝中期,却开始走下坡路。嘉靖年间,倭寇肆虐沿海地区,乌泥泾镇因无城防,为倭寇所破,焚掠而无遗,元气大伤。加之该镇河道逐渐淤塞,闸废渡荒。至清代中期,这个曾名扬天下的棉业市镇沦为了普通的乡村。
太仓刘河镇,自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后,凭借着便利的水运,一跃成为江南最大的饼豆油杂粮市场。然而,此后的刘河镇,海口日渐淤塞,商流逐渐不通。最终,朝廷于嘉庆十三年(1808)颁发告示,允许商船靠泊上海。一纸命令,让刘河镇的繁华戛然而止。
进入晚清之后,特别是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战火随着太平军的北上燃及江南地区,并重塑了江南市镇的经济格局。
自明清以来,浙江始终处于缺粮状态,每年不得不从两湖、安徽、四川等地运粮以填补缺口。大量粮食的调入,需要转运和分销的中间市场,而这个历史机遇,落到了海宁长安镇身上。在承担起浙北粮食转运与分销重任的同时,长安镇迎来了繁荣局面。可是,随着太平军与清军的战线推移,长安粮市在战争中严重受损。战争结束后,浙北粮食贸易重镇的头衔不得不转移至硖石镇,长安镇自此从神坛上跌落。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受伤”的江南市镇不胜枚举。嘉定罗店镇“败壁颓垣鞠为茂草,昔之衣绮罗食珍羞者,今则什无一二焉”。苏州的巴城镇原是“五邑通衢”商业重镇,但在战争中,“市廛尽毁,商业大衰”,直到宣统年间才稍有恢复……
有清一代,以“胡丝”为代表的江浙生丝不仅畅销国内,亦为洋人所青睐。鸦片战争后,因关税降低,且临近新的通商口岸(上海与宁波),江南生丝出口逐年呈现增长态势。有着生丝贸易传统的南浔镇,很快就吃到了时代的红利。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清王朝为恢复经济,在江南地区大力推广桑蚕,不少农户逐渐将稻田改种桑树,以致到了同光年间,江南呈现出“栽桑遍野,比户育蚕”的景象。在政策与出口向好的情况下,江南的生丝产业摆脱战争阴影,再次繁荣起来。
当时,商人们云集于南浔镇,几乎将湖州一带的生丝产销全部垄断。南浔镇一时风光无两,成为胡丝的一大贸易中心。生丝贸易带来了更多的人气和商机,贩夫走卒、行商坐贾纷纷进驻,寻求新的商机。据统计,当地市镇人口在巅峰时期曾高达四万,人口的增加使南浔镇在民国初期被升格为市级建制。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图源:摄图网授权
大浪淘沙之后,曾经的江南市镇,命运虽然各不相同,却都带有历史演进的影子。
江南市镇的崛起,本质上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革命。无论是军镇转型、草市升格,还是棉丝产业兴盛、交通集市扩展,都离不开民间智慧的积累与商业活力的迸发。而它们的命运也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危机与机遇往往如影随形。
回望江南市镇的千年历程,仿佛翻开了一部跌宕起伏的经济史诗。从黄道婆一梭一线改变乌泥泾镇的命运,到濮院镇的丝绸商贾云集;从元朝农商并重的自由之风,到明清战火中市镇的兴衰浮沉——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小镇,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叶扁舟,载着无数普通人的生计与梦想,在时代的浪潮中破浪前行。
全文完。感谢阅读,如果喜欢,记得随手点个推荐以示鼓励呀~
参考文献: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商务印书馆,2022年
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
樊树志:《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中华书局,2023年
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
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
李治安主编:《元明江南政治生态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王旭:《论唐宋时期附郭地区的军镇与市镇》,《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
- END -
作者丨朔方见闻
编辑丨艾公子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