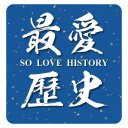刘三解出了一本写三国的新书,叫《汉末之变》,表面上写的是曹操和董卓俩人的经历,内里贯穿的,却是对中平元年(184年)黄巾之乱,至初平三年(192年)一系列历史事件的“重审”。
点击下方图片即可了解详情↓↓↓
在这之后,还会有一本着重讲述初平三年(192年)至建安三年(198年)期间史事,以刘备、吕布、公孙瓒等人物贯穿的作品;以及一本自建安三年(198年)至建安九年(204年),围绕官渡之战、袁氏覆灭事件,包含袁绍、曹操、袁谭、刘备、孙策、郭嘉等众多历史人物的作品。
三者合一,方为之前预告过的《魏阙》,意为魏史之缺。
因此,这本书并不是人物传记,既然没有全面概况曹操、董卓人生的雄心,也没有再评价人物的兴趣,关心的是“事”,而不是“人”,写的是历史,而不是故事,更直白地说,三解在提问,在质疑,在拷问,并提出三国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44元
点击购买↓
用框架分析理论看三国史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这种可能性的论证,在很多书评中,被斥之为“阴谋论”,而非合理推测;或是,作者故作惊人之语,意在“翻案”。
对此,三解无意争论,毕竟如果在表述上,把一些结论的叙述,换成商榷性的学术语言,或许一家之言看起来就没那么扎眼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些未尽之言,书里确实没讲清楚,正好在这里弥补一二。
1974年,社会学家欧文·戈尔曼出版了《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第一次把“框架”的概念引入了社会科学,
戈夫曼的看法是,“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社会事件原本混乱无序,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正是框架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辨识和标识社会事件与信息。
说得更白一些,就是“事件不会自己说话,要从它们本身所嵌入的框架中呈现意义。”
这个概念,对于新闻传播学影响深远,而三解的职业经历中,也有那么十来年算是新闻从业者,略有接触,故此,虽然《汉末之变》只是一本断代历史的通俗作品,实在不宜写得过于艰深,没有引入多少学术词汇,但是,在序言之中,以“英雄合影”的截取局部作比,其实已经体现了戈夫曼的理论思路。
具体来说,《汉末之变》的书写之中,包含了三重“框架”的含义:
其一,大众对于三国的认知,基于《三国演义》及周边的文本、影像经验,建构的一重认知框架,并由此理解的“三国”;
其二,学者对于三国的认知,基于《三国志》及裴注、《后汉书》《资治通鉴》《后汉纪》等文本历史书写,建构的一重认知框架;
其三,上述两重框架的前提,汉魏禅代之际,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作为现实政治解释的主宰者,建构的叙事框架,与散落在敌国和士林的、不同面相的大事记忆,经过长时间的互动发酵后,形成的一重认知框架,它在当时既是历史,又是现实。
简单的总结,就是大众的、学术的、政治的三重框架,其中,政治的框架又zui为重要,为什么呢?
因为政治的框架是一整套现实解释的总集,是学术框架的文本基础,也是大众框架的想象源泉,其表现,则在于与“翻案”相关的四个字——盖棺定论。
44元
点击购买↓
框架与历史的真实
现代人谈历史,强调的是事实、真实,故而对史官秉笔直书、一字不改,异常推崇,可是,齐太史简和晋董狐笔,记录的都是档案,顶天是国史,是藏在内府中的机密文件,目的并不是为了传播,更不是我们熟悉的史书。
真正意义的史书,是《史记》、《汉书》,他们有一整套的,作者主导的价值判断,本身就是“框架”。
可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
无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雄心如何之大,号称,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五百年后有自己,“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要当仁不让,司马迁更是要一本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可是,当上大夫(詹事)壶遂问难,“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你现在生当圣明天子之世,为什么也要作《春秋》,你想干嘛?
太史公的回答只能是:“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在这个调子的保护下,我们才有幸看到了这部巨著,可到了东汉末年,在王允这样的正面人物眼中,《史记》是什么呢?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谤书的意思,李贤注释说的很清楚,但凡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这种意识是凭空来的吗?当然不是。
自东汉初年开始,私撰国史就是重罪,班固在父亲班彪死后,回到家乡写《汉书》,就被人上书汉明帝,举报他“私改作国史”,皇帝的反应是,下诏抓捕班固入狱,并抄没家中藏书。这个罪有多大呢?班固家人比照的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也就是,如果不能说服领导,你写书是为了领导好,就是死刑。班固得以幸免遇难,还是靠他弟弟班超去告御状,汉明帝也看了他完成的作品,没什么犯忌讳的,这才饶了他,收编进了体制内,修国史去,等他给汉光武帝写完本纪,又写了28篇国史传记、载记,才算考察完毕,允许班固把自家的《汉书》写完。
可见,自东汉初年开始,汉明帝就已经意识到垄断历史解释的重要性,之后各代皇帝更是不断招纳名儒,编修国史,以掌握对个人、事件“盖棺定论”的权力,而所有的文本结论总集,就是对东汉王朝历史的“框架”确认。
因此,当我们阅读东汉王朝史料基础上,编撰出的多家《后汉书》《汉后书》《后汉纪》作品时,就会发现,其中的主要内容,与《史记》《汉书》大不相同,军国重事的细节很少,充斥着“祥瑞”、“灾异”、“三公任免”、“道德模范”,虽然有一些政治斗争的记载,可整体来看,还是为了盖棺定论、明确政治责任,一个儒家理想国的轮廓,跃然纸上。
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44元
点击购买↓
符号学与拟剧论
拟剧论是社会传播学的概念,也是欧文·戈夫曼首创的理论,它的核心观点就是:人生是一场表演,社会是一个舞台。
戈夫曼认为,人际传播的过程就是人们表演“自我”的过程,但这个“自我”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经符号乔装打扮了的“自我”。符号,本身就具有欺骗性,符号能力的获得使我们永远地脱离了单纯的物理世界。
将这几个概念套用在上述历史时段之内,很多问题可谓迎刃而解。
之所以东汉的历史文本表现出强烈的儒家特性,好像与司马迁笔下的西汉世界迥然不同,并非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社会变革的巨大鸿沟,而是经历过西汉末年的儒学大扩张,东汉王朝的统治者,获得了一整套的儒学符号体系,其集大成者,就是《白虎通德论》。
而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面对的文本信息、社会信息,仍然是未经儒学符号改造过的物理世界,或着叫,多元化的符号世界,因此,司马迁所作的《史记》,还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以及百家之言。
到了班固的笔下,这些旧的符号,被一一摒弃。班固甚至对司马迁的经历颠倒黑白,声称司马迁是在身罹腐刑之后,才开始著史,以强调其“谤书”的特性,唯有他班固真正懂得汉德,“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朱维铮. 班固与《汉书》--一则知人论世的考察[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20-28.)
说得直白些,就是司马迁表达的是他的时代,多元化的符号世界,还没有被皇权完全垄断的“框架”(frame),而班固的作品,则是新的符号世界建构的一块砖瓦,是正在建构的儒学符号世界的附庸,是新的皇权垄断“框架”形成的过程(framing),那么,《东观汉记》《后汉书》《后汉纪》本质上都是,东汉皇权垄断“框架”成型后的结果(frame)。
在“框架”成型之后,东汉政坛的主导者们在社会的舞台上,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表演,按照戈夫曼的研究,就会有四种形式:
1、理想化表演。这种策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掩饰。“表演者会掩盖或部分地掩盖与他自己理想的形象不一致的活动、事实和动机”,以便集中展示自己理想化的形象。
2、误解表演。富人装穷,流氓扮绅士都是误解表演的例子。
3、神秘化表演。与互动方保持一定距离,使对方产生一种崇敬心理的表演称之为“神秘化表演”。
4、补救表演。
如果您细读《汉末之变》的文本,就会发现,曹操和董卓的经历复原中,三种表演都可以对号入座。比如,曹操在诸侯讨董战争中,与鲍信、鲍韬两兄弟和卫兹的28000联军,大败于徐荣率领的抄掠偏师,书写记录中,不但隐去了徐荣的兵力,隐去了鲍信兄弟的参与、鲍韬的战死,强调了他领兵数千(《让县自明本志令》),还要渲染,曹操的力战阻止了徐荣攻打酸枣的联军大营,从而让人误会,他是以寡敌众。这就是“误解表演”。
再比如,曹氏家族的三易其祖。曹操(《家传》)和曹植(《武帝诔》)父子的文本,一起将自家的祖宗,从黄帝的封国后人,变成了周文王的儿子曹叔振铎,从而比附他自己的周文之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而他的孙子曹叡,因为汉魏禅让的形式,又将自己的祖宗挪到了舜的名下(汉为尧后),就是要把尧舜禅让的理想故事坐实,无疑是,同一个戏码又演了一遍。
无独有偶,出身关西的董卓,对于重建前汉的关西主体政治的兴趣,也相当浓厚,他不但要比附汉元帝时代的灾异迁都消灾,还在迁都长安后,担任太师、尊称尚父(姜尚),比附西周王朝的周武王以姜子牙为师,扫平天下,奠定八百年的周朝天下。这些,都是“理想化表演”的实例。
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作秀”式的行为记录和事实改写,完全可以用心理学中的“框架”来解释:即框架是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中安排信息,以至于一个议题的某些东西在个人的认知资源中占有更大的部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这一部分东西在影响个人的判断和推断上变得很重要。
具体来说,东汉皇权确立的儒学符号体系经过100多年的统治,已经深入士大夫的骨髓,董卓这个外戚身份的武将,曹操这个宦官之后的士人,并不能免俗,尤其是他们面对社会进行表演时,仍会下意识地趋近于理想。
可两者又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44元
点击购买↓
合理推测与阴谋论
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汉末之变》中,存在三重框架,大众的、学术的、政治的,现实中的事件,只是三重框架下的意义载体,可作为历史研究,研究的核心对象,或者说,无限趋近的目标,只能是现实中的事件还原。
故此,对于大众的认知,三解主要通过一些基本事实的辨析,作出回应(如董卓没有篡位行动);对于学术的认知,三解主要通过提出记载之间的矛盾(如曹操起兵时间问题),或是文本与常识之间的冲突(如130万青州黄巾的吃饭问题),或是对史料的补充解读(如董卓弟弟担任外戚官职),要求“重审”这些问题;对于政治的认知,却是zui难的,三解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有限的史料,作出合理推测。
问题是,合理推测和阴谋论的界限,并不容易区分,在书评里,有一位朋友就把阴谋论的定义是“虚浮”+“猥琐”,论证虚浮,且用猥琐的思维去猜测历史的真相。这可以说是相当让三解破防的指控了。
究其原因,应该是《汉末之变》对于曹操早年经历的考证之中,夹杂着一些导向“理想化表演”和“误解表演”结论的推测,这些推测隐含着否定曹操能力的意味。
对于大多数三国读者来说,批判曹操的人品、家世,尚在接受范围内,可如果否定曹操的能力,就算是批了逆鳞了。
其实,这里三解要解释一下。对于曹操这个人,我没有否定或是翻案的兴趣,本书之所以如此这般,是在探究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
有志于复兴汉王朝的董卓,也曾依照当时世界观和舆论中“正确”的道路,进行“理想化表演”,为什么会一败涂地?
而曹操的经历,哪怕剔除掉《汉末之变》中一些带有推测成分的经历,只看事实考证清晰的,他的前半生表现和立场(结交声名狼藉的桥玄、胁迫许邵求评、由宦官养子举孝廉、冒认诸侯首义),不说与舆论中的“正确”背道而驰,也是乏善可陈,为什么他会笑到最后?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有一段新旧道德之论,恰可作为注脚: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又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育,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在《汉末之变》的结尾,我曾对董卓的必然失败,作出了同频的解释,那就是,董卓本质上是旧道德的笃信者,因为他虽然出身陇西边地,却并没有如普通凉州人一样,被困在戍边武将的身份之上,因为他还有一重身份,就是董太后的族人,外戚新贵。
东汉特有的外戚政治和宦官政治一样,是底层士大夫的晋身捷径,哪怕是“身自屠羊”的何进,也能够名列大儒、帝师杨赐的门墙,更何况战功卓越的壮健董卓,在桓帝驾崩、灵帝即位之后,立刻走上了官场的快车道,之后,仕途更是一路顺遂,位列公卿。
可以说,他是妥妥的既得利益者,汉献帝本人更是和他多了一重亲属关系的羁绊。
可是汉王朝的统治危机愈演愈烈,天下归恶于宦官,以及桓灵政治的余毒,维持旧秩序,总要刮骨疗毒,可董卓与党人的同盟,一刀下去,只看到伤口更大,再下刀,血洞更大,皇权持续扩张造成的恶果,通过斩断皇权的爪牙,非但不能治本,反而让皇权和中枢无比虚弱,沦落到了蜗居关西,需要再打一次统一战争的地步。
董卓和王允,从一呼百应到众叛亲离,只有一线之隔。当他们是秩序破坏者时,有无数的同盟、战友,当他们变身为秩序的修补者时,就沦落为孤家寡人。因为自他们代表皇权开始,就已经在伤害同盟者的利益,直到对方忍无可忍,或是肉体被消灭为止。对方当然不想死,那么,自然会竭尽全力地反抗。
那么曹操呢?
他的成功在于,他的家族,他自己的出身,他的出仕,他的宦历,恰恰是旧秩序下的边缘人,既可以让他比普通士大夫,拥有快人一步的优势,比如曹操二十岁举孝廉,和韩遂的父亲是同年,可另一方面,他和真正得势的顶级权贵,又隔着一座泰山。
前者让他有资格成为一个秩序的破坏者,后者让他有意愿和愤怒,一直做一个秩序的破坏者,而不需要顾忌任何的既得利益,毕竟连他祖父传来下来的费亭侯,都是在他父亲死了两年之后,他举兵入洛阳迎献帝时,才受封的。说白了,本来手里什么都没有,砸烂坛坛罐罐也都是别人家的,他有什么心理障碍呢?
他就是陈寅恪先生笔下的“不肖巧者”,新旧道德操弄者,历史逆淘汰的大赢家。当他胜利之后,又因其巧,而对自己的历史形象无比在意,希望自己能够以符合儒家符号体系的理想形象,出现在文本记录上,书写属于自己和自己家族的新“框架”。
当然,这个故事并没有写完,还有第二和第三部,里面将有更多的事实还原,敬请期待。
44元
点击购买↓
*以上内容为广告推广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