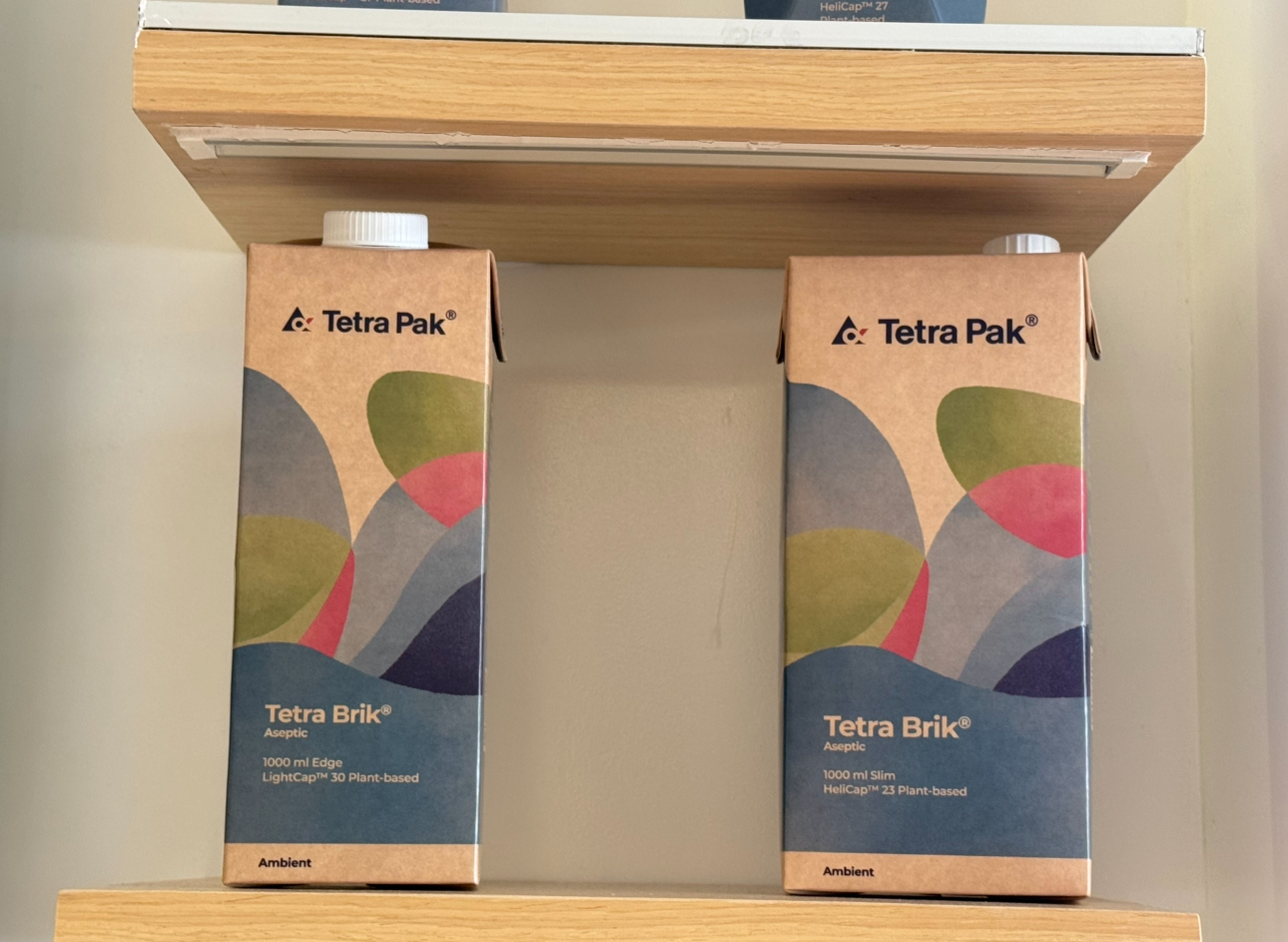屋顶上,太阳能光伏面板、热回收管道与更节能的冷冻机高效运作;车间里,除尘器和传送带已完成节能优化,仓库照明系统也已升级改造完毕;物流区,电叉车的身影取代了传统叉车,进一步减少排放……
涓绿成流,让减碳落到实处。10月22日,食品加工与包装解决方案提供商利乐公司宣布位于江苏昆山的一体化生产服务基地获得TüV南德意志集团颁发的碳中和核查证书,成为其中国首个“碳中和”生产基地;同月,该基地又入选“苏州市零碳工厂建设工作成效突出企业名单”。这份“双荣誉”背后,不仅是一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更折射出全国零碳园区建设的浪潮:截至今年8月,全国28个省份出台专项规划,累计启动127个零碳园区项目,零碳战场正从“概念”走向“实践”,成为城市与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阵地。
零碳破局▶▷
“开源节流”三重奏
“‘碳中和’基地不是‘零排放’,而是先把排放尽量降低,因为这个‘碳中和’是动态的,后面可能还会再降一点。”TüV南德意志集团大中华区管理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解释,这正是行业公认的“净零碳”路径,利乐昆山基地的探索,恰是这套逻辑的生动实践,可归纳为“三大狠招”。
第一招是能源“换血”。2023年起,基地逐步淘汰高排放设备:液化石油气叉车换成电动款,厨房灶具改为电气式,充电配套设施即将完工;天然气锅炉被地源热泵取代,靠土壤中的自然热能满足部分供暖需求。更关键的是可再生能源的加码——2022年底投用的光伏面板发电系统,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发电超3800兆瓦时,相当于减少2690多吨碳排放,2025年底新增面板启用后,这一数字还将提升。
第二招是智能“降耗”。2023年,基地上线能源监测管理系统,实时追踪车间、仓库、办公楼的能耗数据;2024年,作为首批试点,又启动设施能源管理合作项目,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定位减排机会。水资源管理上,2022年食品设备工厂启用废水回用项目,用RO膜技术处理生产废水,再用于冷却塔补水和污水处理配药,每年节水近2000吨;废弃物处置上,改用热处理洗版技术,从源头减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产生,还避免了蒸馏残渣的二次污染。
第三招是循环“魔法”。比如基地抓住包材生产的工艺特点,将后段复合工段产生的高温烟气余热回收,输送到前段印刷工艺加热,每年能节约14万立方米天然气,相当于减少280吨碳排放;同时收集空压机运行时产生的余热,补充办公楼采暖和生活热水,让“废热”变“宝热”。
一套组合拳下来,2024年昆山基地碳排放降至3388吨,再通过购买碳汇抵消剩余排放,最终叩开“碳中和”大门。“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遵循国际标准(如PAS 2060)的系统性过程,从承诺目标、盘查碳足迹,到落地减排、抵消剩余排放,每一步都要经得起核查。”TüV南德意志集团大中华区管理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强调,而贯穿始终的核心原则是“减排优先,抵消为辅”——碳汇是“补位”,绝非“替代”。
深水区挑战▶▷
从“开关灯”到“精算师”的转型阵痛
利乐的零碳探索,也映照出行业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两年找我们做碳盘查、碳中和认证的企业,数量是指数级增长。”TüV南德意志集团大中华区管理服务部相关负责人透露,背后既有国内外政策推动,也有供应链压力——国际大品牌作为“链主企业”,正把减碳要求传导给上下游。
“目前很多减碳标准、规范是针对链主企业,这就要求他们去管理自己的供应商,对供应商而言,如果不和链主企业一起减碳,那可能没办法进入其供应链,或者很容易被替代掉,所以价值链的传导是非常快的。”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会长张亚龙指出。
这种压力下,企业减碳呈现明显分化:头部制造企业大多完成碳盘查,有清晰的碳中和路线图,还能推动供应链协同减排;但大量中小企业仍在“启蒙阶段”,既缺技术,又缺资金,尤其是高耗能的制造类中小企业,减排难度更大。而像利乐这样的大企业,虽已跨过“入门关”,却走进了减碳的“深水区”。
“早期减碳,靠‘开关灯’、换低能耗设备、用绿电就能见效果,这些容易的措施现在基本都用遍了。”利乐大中华区公共事务总监、碳核算项目负责人张浩玮坦言,现在要找的是“潜在又有效”的减排点,这就需要“精细化管理”。比如基地部署的能源监测系统,能追踪到每一条产线,甚至每台设备的能耗。
TüV南德意志集团大中华区管理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进一步分析,“精细化”面临三道坎:一是数据要“细”,从组织级碳盘查,深入到每款产品、每个工艺环节的碳足迹测算;二是技术要“新”,需要碳捕集、新型环保材料等突破性技术;三是范围要“广”,从原材料开采到产品报废回收的整个生命周期(Scope 3)实现碳排放管理,还要拉着上下游一起减。
利乐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利乐中国统计的价值链上下游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约1003030吨。在包材产量增长的背景下,包材原材料排放量相较2019基准年下降9%。
零碳浪潮▶▷
从园区“细胞”到城市“竞争力”
利乐昆山基地的认证,并非孤例。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及“零碳园区”,2025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发文推进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9月以来碳市场扩围、新型储能政策密集落地,10月《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更是明确,零碳园区项目最高可获核定总投资20%的资金支持——政策红利下,零碳园区正从“试点”走向“规模化”。
这场浪潮的背后,是零碳园区角色的转变:它不再是单纯的“环保工程”,而是城市竞争力的“绿色单元”。张亚龙指出,中西方零碳园区发展路径不同:西方侧重绿色建筑与生态设计,中国在绿电应用、新型电力系统上有优势,但国内标准国际化不足,部分园区虽获本土认证,却难满足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要求,这给跨国企业带来合规成本压力。
但压力也暗藏机遇。“以前园区靠劳动力、原材料成本吸引企业,现在这个优势在减弱。”张亚龙说,随着碳标签体系普及,零碳园区能为产品“碳足迹”背书,“未来园区的竞争力,会从‘拼成本’变成‘输出绿色标准’”。深圳前海、天津港等园区已开始对标国际标准,把“零碳”打造成招商“名片”。
而零碳园区的建设,从来不是“单打独斗”。政府定指标、科研机构供技术、园区运营商管长效、企业落措施,这种多方协同模式已在多地见效。成都利用水电优势,结合社区更新与住宅储能技术;深圳天安云谷依托科技企业集群,实现“生产低碳+生活低碳”的产城融合——不同城市的探索,都遵循“因地制宜”的核心逻辑。
当然,挑战仍在:国内标准与国际接轨、传统产业转型、公众参与意识提升,都需要时间突破。但正如张亚龙所说:“零碳园区是城市的‘细胞’,当无数‘绿色细胞’连在一起,零碳城市的图景才会真正清晰。”从利乐昆山基地的屋顶光伏,到全国127个零碳园区的实践,一场关乎未来的绿色革命,正从每个“细胞”里生长开来。
南方+记者 周中雨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