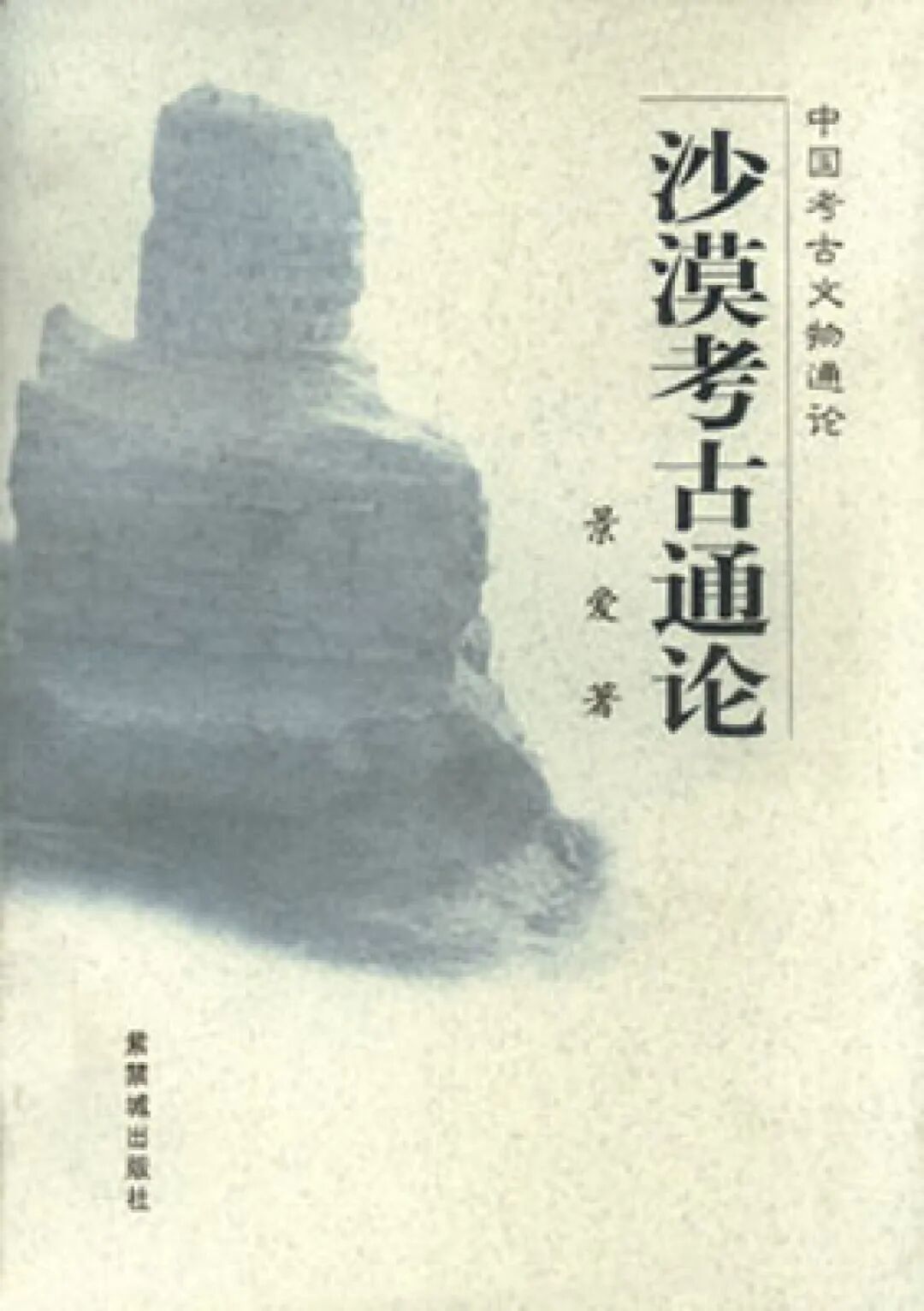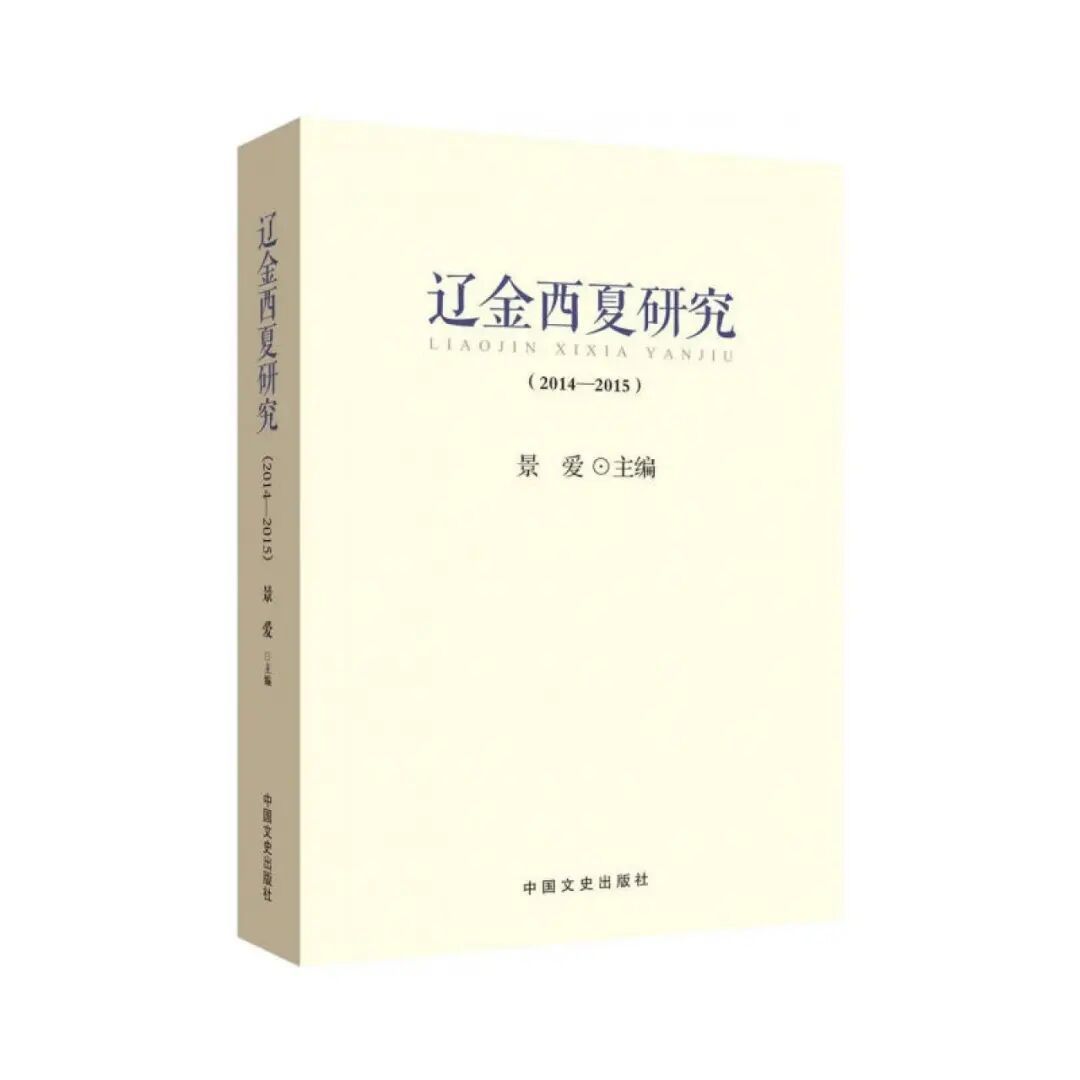▲景爱 图/资料图片
“沙漠考察的危险性、刺激性,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任何科学成就的取得,很难一帆风顺,往往与危险交存。越是艰险的地方,科学家往往奋勇争先。”景爱回顾沙漠考古的经历时说,“我想人生的价值即在于此。”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韩茹雪
车子在沙漠中小心穿行,前方出现一片黄色沙地,沙地上掩埋着成片枯死的胡杨。树干树枝都是黑灰色,光秃秃的。在秋风的吹动下,胡杨左右摇曳,呼呼作响,地上已见不到一丝绿色。这里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被称为“生与死的分界处”。这是景爱第一次看见连片的死胡杨林,他将这些细节一一记录在册。
景爱一生与沙漠结缘,多次深入沙漠腹地。他的沙漠考察行程累计达6万余公里,出版了《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警告:北京沙尘暴》《尼雅之谜》《沙漠考古通论》等著作。面对学界与新闻界称其为“沙漠考古第一人”,景爱谦逊表示:“我不是什么‘家’,而是一个‘者’,即普普通通的考古工作者。有机会跑遍中国北方的大沙漠,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幸运和乐趣。”
“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进行交叉研究,这是我的终身追求。我是一只眼睛看社会科学,另一只眼睛看自然科学,这样可以避免单一学科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景爱曾这样总结自己的研究,他一生笔耕不辍,在沙漠考古之外,还在文物与古文献整理研究、长城研究等领域有建树。
2025年12月24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发布讣告:我国古文献与考古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原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退休干部景爱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2月21日1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沙漠有一颗冷酷的心
“凡进过沙漠从事科学考察的人,都知道沙漠有一颗冷酷的心,”景爱曾这样撰文,“它对一切生命都充满了敌意,它想吞噬那些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其中也包括人类。”
唐代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一段记载:“沙则流漫,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道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
景爱是深入沙漠的队伍中的一员。景爱出生于1938年,辽宁本溪人,1963年从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在黑龙江省博物馆和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此后陆续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深造,1981年分配到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后并入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
1970年代末,景爱师从历史学家陈述先生攻读辽金史,后因工作关系接触考古学,转向沙漠考古。景爱真正与沙漠接触,是在1973年。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出现了边界冲突。根据上级有关领导的指示,景爱和另外一些同行奉命到中苏边境地区考察。以考古材料证明黑龙江以北、额尔古纳河以西、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在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
景爱进入了呼伦贝尔草原。在他的想象中,呼伦贝尔草原应当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当时流行的草原牧歌,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来到呼伦贝尔草原,景爱所见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触目皆是败草黄沙,只有在河边湖畔,才能见到灌木和蒿草。不要说牧草掩盖不了牛羊,就连一只老鼠跑过,也会看得清清楚楚。”
这让景爱感到困惑,他不知是古诗记载有误,还是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从此,他走上了沙漠研究之路。多年后,景爱这样回忆当时的选择:“一个人的命运很难由自己安排。社会的需要,常常把一些人推向他自己梦想不到的地方。”

▲2005年10月,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工人顶着风沙维护固沙植物 图/视觉中国
此后数十年间,景爱几乎踏遍了中国北方沙漠,曾两次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经过多年的研究考察后,景爱提出“沙漠化二重性”理论,强调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是社会现象,明确指出沙漠化“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在历史时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自然则处于被动地位,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日益加大。自然因素只是为沙漠化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人类活动则是导致沙漠化产生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科学论断为国内外广泛采纳和接受。他因杰出的研究被誉为我国“沙漠考古第一人”,其事迹被收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曾有人认为治沙即种树,但景爱主张应先读懂土地的“记忆”。他通过考古发现,许多现代沙地原是古代农垦区,生态系统早已脆弱不堪。基于古代遗址的研究,却始终映照现实、指向当下——这正是景爱一以贯之的学术路径。他的《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成为国家“八五”重点专著,直接推动“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向历史敏感区倾斜。
打假“克隆”长城
在沙漠考察活动中,景爱频频接触长城和边壕,在长城研究领域贡献卓著。
长城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建筑工程,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的象征和文化标志,“不到长城非好汉”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一句话。
景爱注意到,在“以长城为荣”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没有长城的省区有些焦躁不安,想方设法寻找长城、“克隆”长城,以增加旅游资源。他举例,云南是没有长城的省份,却请了一位北京的教授去寻找长城。教授不负所望,真的找到了一段长城,称之为云南长城。当地许多专家学者则指出,所谓的云南长城,只不过是古代土司修筑的围墙而已。
曾有报道说,在云南北部山区的岩洞中发现了新长城,等待专家学者去鉴定。“岩洞中筑长城,是为了防御谁?难道岩洞也成了古战场?这是耸人听闻的天方夜谭”,景爱对这类事情直接表达不满,“不真实的长城应列入学术打假之列。”

▲2024年7月4日,北京箭扣长城五期保护修缮项目的工作人员进行长城修缮 图/视觉中国
在景爱眼中,将山险、边壕说成是长城,人工“克隆”长城,都属于失实行为。在民间争抢之外,景爱还注意到官方也有宣传错误。2001年由一些地方审定通过的小学语文第七册中,收有刘厚明撰写的《长城砖》一文,引用美国宇航员的话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只能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
此文是根据有关媒体报道编写的,美国的宇航员曾解释,那是有人误解了电视采访,他的原意并非如此。曾有人问我国第一代宇航员杨利伟:是否在航天飞行中用肉眼看到了长城?杨利伟明确表示,他没有看到长城。类似失实的宣传,在国内外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长城早、长城长,固然是好事,但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能将不是长城的天险、边壕也说成是长城,更不能无中生有去‘克隆’长城。”景爱撰文指出。
多年从事研究的专业素养让景爱知道,长城误区的存在与长城研究工作的薄弱有直接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景爱一直从事沙漠考古研究,即以考古学手段研究沙漠变迁。在考察活动中,景爱频频接触长城和边壕。中国古代的长城、边壕主要分布在北方沙漠草原地区,在那里可见到各个不同时代的长城、边壕。由于气候干燥、人烟稀少,长城和边壕的遗迹保存得相当完好,犹如露天博物馆。
当时,景爱对所接触的长城和边壕做了仔细考察研究,因为这些遗迹是解读沙漠历史变迁的关键密码。
走出长城研究的误区,才能更好地保护“长城”作为一种精神符号的文化价值。景爱从研究的视角出发,觉得要准确认识长城,不仅要明确其起止走向和长度,还应知道其修筑的历史背景,以判明其历史地位和科学价值。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长城整体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基于这种认识,景爱把长城研究的成果整理出来,写成了《中国长城史》,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有高水平的长城研究专著问世。
《中国长城史》以编年史的体例展开,涵盖春秋战国至明代长城的修筑历程。研究采用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引用《史记》《汉书》《明史》等史料,并整合敌台、烽燧、关隘的考古数据,形成多维度论证体系。例如,书中关于北魏柔玄镇地望的推断,在2025年尚义县土城子城址考古发掘中得到实证。书中将军事防御工程作为主线,分析历代长城的地理分布、形制特征及战略部署。
作为长城史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中国长城史》被多部学术论文及文化遗产报告引用。在国家线性文化遗产网络构建研究中,该书被列为军事工程类核心参考文献,论证长城的时空连续性特征。
关于在长城这一新领域的跨越式研究,景爱写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只有大家共同研究,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实现接近真理之追求;故步自封,满足现状,不利于学术发展,应在摒弃之列。”
吾将上下而求索
1998年,景爱参与起草《行动起来,拯救黄河呼吁书》,联合近两百名院士共同签名,推动全社会关注生态保护,产生广泛影响。
自1972年黄河下游首次断流至1999年,在28年间,黄河有22年出现断流,累计断流天数达1079天。
1992年,黄河断流70天,山东滨州、东营4000公顷农田无法播种,500万公顷夏苗干枯死亡;1996年,胜利油田因黄河断流无水可注,数百口油井被迫关闭,半年经济损失达3亿元;1997年,利津水文站记录断流13次累计226天,干涸河道上溯至河南开封陈桥,断流长度达704公里,黄河近300天未能流入大海。
多年的户外考察经历让景爱对生态环境保护有更深的体会。他在《警告:北京沙尘暴》中提出,若不正视人地关系失衡,历史的悲剧或将重演。纵观他的学术生涯,能看到鲜明的现实关怀色彩。他的考古不仅是对过去的追忆,更是为未来提供历史镜鉴。这种将学术研究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的精神,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

▲景爱(前排左二)出席《求索录》出版座谈会 图/资料图片
《中国文物报》记者冯朝晖曾撰文,回忆他参加景爱新著《求索录》出版座谈会的情形:多年未见的景爱还是印象中的样子,文质彬彬,精神矍铄,说话慢条斯理,尤其是那纯天然的满头乌发,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位80岁出头的老者。
2020年9月底,年逾八旬的景爱仍然坚持深入沙漠考察,并撰写相关文章。新出版的《求索录》正是景爱此前五十多年学术生涯的见证,该书收录了他出版的著作以及发表的文章,共350余篇。
会后合影时,冯朝晖才发现景爱的腿已经不太灵便了,需要拄着拐杖,由人搀扶着缓慢前行。景先生的老朋友们说,这是他年轻时徒步考察走过的路太多了,把这辈子该走的路提前走完了。谈及景爱的另一本辽金史研究著作即将出版,在场的人纷纷表示期待与祝贺。景爱回答,“只要我的精神还行,还能动笔写字,我就会继续研究下去,写出更多对社会有用的文章。”
冯朝晖与景爱相识多年,他记得景爱的座右铭:知识既来自书本,又出自脚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景爱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沙漠考古后继有人,将沙漠考古推向更高峰。
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孙兴民曾解释《求索录》名称的由来。在收录景爱发表的著作和文章时,他被景爱在科学研究中的努力与执着打动,很自然就想到了屈原的那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所研究员林荣贵和景爱同是历史学家陈述先生的研究生。他提到,在陈述先生诸多研究生中,真正坚持辽金史研究的人不多,只有景爱最终坚持下来,做出了成绩。在辽金文物与古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景爱笔耕不辍,出版了《辽金西夏研究》《金上京》《金代官印集》《金代官印》《中国边疆民族文物集粹》等作品。
“沙漠考察的危险性、刺激性,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任何科学成就的取得,很难一帆风顺,往往与危险交存。越是艰险的地方,科学家往往奋勇争先。”景爱回顾沙漠考古的经历时说,“我想人生的价值即在于此。”
(参考资料:景爱《沙漠考古通论》《中国长城史》《寻找被湮没的文明:沙漠考古札记》、北京日报《“沙漠考古第一人”景爱<求索录> 出版 收录350余篇著作》、中国文物报 冯朝晖《景爱先生 <求索录> | 一位考古学者的探索之路》。)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